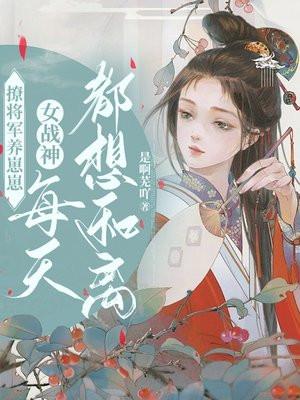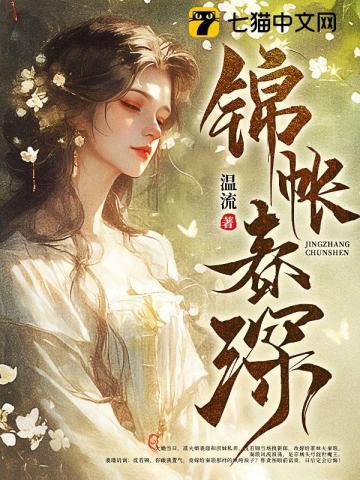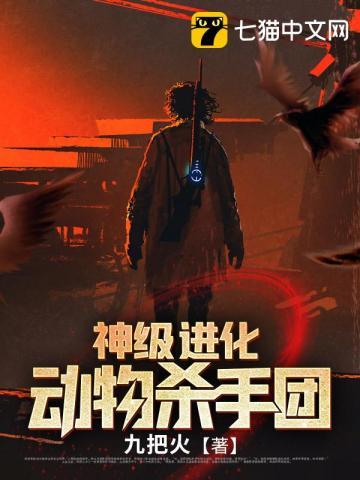墨坛文学网>狮子山下

《狮子山下》第十九章
相邻推荐:媚妾为后 京圈少爷的公用狗腿 换巢鸾凤 抢我命格?全京城都被真千金打服了 这种妹妹该挂哪科? 大学时的死对头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你的雪人能活多久 致小天使 我真没想结婚啊 野渡 路过的怪物都要踹一脚 摆烂,摆烂,摆烂!!! 从华夏神话开始碾压星际 我读动物心声直播看诊 喜欢山,喜欢海,喜欢你。 明日如昼 北宋小丫鬟 晨昏界限 从赤月之夜开始横扫赛博世界 荒唐 第一天骄苏月夕、主角: 秦方 苏如是、秦时记事秦时姬衡
(19)
林念知是在一首《Last Christmas》里走神的。
那天下午,她刚结束导师安排的访谈汇报会,走进大学站正好是五点半,天已经有点暗,空气潮湿,像是刚洒过一层薄雾。她背着电脑包,从扶梯口缓缓走下来,斜对角的街头有个男生在弹吉他,前面放着一个纸盒,写着“为梦想努力中,谢谢支持”,字体工整,有点像中学的美术字。
他唱得不算好,咬字带着点腼腆,调子也浮浮的,但他眼睛闭着,唱得专注。
林念知本来只是路过,脚步却在副歌那一句停了下来:
Last Christmas, I gave you my heart…
她忽然想起几天前的夜晚,林思颖抱着靠垫,说“其实我只是想让人知道我还在”时的样子。那句话像一颗糖,表面是甜的,但只要含得久一点,就开始发苦。
林念知没多想,只是把包拉紧了些,地铁站里商铺过道两边挂起了圣诞装饰,天花板上多了几圈红金相间的纸花环,广播换了频道,播的是BGM版本的《Jingle Bell Rock》,轻飘飘地在地铁站里盘旋。
她不是不喜欢圣诞节,只是觉得在香港这样热闹得太快的城市,连节日都像是为消费而生的。商场的布置比学校的通知早两周,咖啡店的圣诞杯也在十一月中就换上了红绿配色。她好像总是比这些节奏慢半拍,还没反应过来,街头就已经全换了灯饰。
林念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唱歌的男生。他还在唱,嗓音被风吹得有点破,前面的纸盒里多了几张二十元纸币,还有几枚硬币。
那一瞬间,她忽然觉得有点奇怪。
——林思颖好像真的没有再提过那晚的事了。
不是避而不谈,而是真的像忘了一样。她一开始以为那只是林思颖的防御机制,后来发现,她是真的恢复得很快。像水滑过光面的玻璃,不留下任何痕迹,也不需要回头确认什么。
倒是她自己,一直在想。
她不是没试着告诉自己那晚不过是林思颖的一次短暂泄洪。也许她说那些话时确实是真情流露,但说完了,也就过去了。可林念知就是放不下。她总是这样,哪怕只是听到一个擦边的片段,也会一再回想。
“无脚鸟”。
她那晚回房间后,盯着电脑发了很久的呆,指尖落在键盘上却什么都没敲出来。脑子里一直盘旋着那句话。无脚鸟只能飞,一辈子只能落地一次,而那一次是死。
她其实不懂这句话是不是形而上的比喻,也不清楚林思颖说那句“我就是想让人知道我还在”时,究竟是真心的自白,还是一场精巧的情绪输出。但她记住了。像记住了一场梦境里的微光,醒来后却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想象。
地铁进站的风把她拉回现实。她快步上车,在车门关上的一瞬间抓稳吊环。车厢里已经亮起了红绿灯带的投影,天花板贴着商场广告的圣诞贴纸,连报站声都换成了节庆语调,车内广播用轻快的语气提醒大家“冬至将至,记得同屋企人食餐饭”。
林念知低头掏出手机,看了眼屏幕。12月13号。距离圣诞节还有十二天。
她忽然有些迷茫。时间过去得太快了。
这一年她好像什么都做了,又好像什么都没做。论文写了一半,访谈做了不少,兼职补习没停过,生活每天都被填得满满当当。但她说不上自己是不是“前进”了。就像在一条不断移动的扶梯上,脚步再快也只是原地踏步。
她靠在车厢墙上,闭了闭眼。忽然有点想家,又不是真的想。她只是想到,她妈每年冬天会炖一锅萝卜牛腩,饭桌上会放那只有点磕破了的搪瓷碗,弟弟会边吃边看手机,而她爸,会在新闻频道前打个盹。
可这一切她都不想再回去了。也不能。
回去之后,她依旧会被问“有没有想清楚前途”,会被拿去和“那个谁家女儿”比较,会被提醒“你读书读那么久也没什么用”。
那样的家,是她一心想逃离的地方。但有时候夜深了,又会忍不住想起那里灯光昏黄的厨房和阳台上晾得半干的毛衣味。
她也是无脚鸟吧。只是飞得不那么快,翅膀也不够有力。
……
灯一闪一闪,地铁穿出隧道时,窗外是隐隐约约的夜色。林念知拉紧外套,等车一停就跟着人流下了车。
刚过六点半,红磡已经起风了。她从车站出来,风一阵阵地灌进围巾缝里,冷得像用力往耳朵灌水的气流。她本来想着要不要绕去超市买点蛋饼皮,想起冰箱里还有三颗西柚没吃完,便放弃了念头。
从地铁站走回都会轩的那条路,已经陆续挂起了圣诞灯串。那种白金色的小灯泡绕着栏杆,间隔地插着几个商场赞助的红色贴纸,上面写着“Festive Season at oa”。但天色太灰了,灯光显得有些无力,像是硬要从冷空气里挤出一点“节日气”。
等她刷卡推开门,屋里灯没开,但客厅的角落却亮着一小团金橙色的光——那是林思颖几天前放的那颗圣诞小树。大概一米高,从Daiso买来的,插了几只塑胶球和发泡棉雪花,顶上那颗金星还是歪的。
小树的灯亮着,电池应该是新换的。
餐桌上放着几只包装过的礼物盒,颜色各异,边角都贴了金色的蝴蝶结标签;落地窗下多了一袋超市买的红绿色薄荷味dye;沙发上的靠垫也换了个套子,印着拙劣的圣诞驯鹿模样的三丽鸥角色。
林念知站在门口换鞋,忽然觉得有点恍惚。
她刚才在地铁上还想着“冬至将至”,林思颖已经布置起圣诞了。
她总是这样,速度极快,风格鲜明。情绪好起来的那天,她可以去买圣诞袜、订火锅位、买五包蜡烛做气氛装饰。好像那天深夜她抱着靠垫哭着说“我真的真的好想有人可以因为爱我而无条件迁就我”,是另一个时空的人说的。
林念知换好鞋,慢慢走进屋里。她没有立刻开灯,只是把包放在沙发边缘,站在那株小小的圣诞树前,看着那几颗闪烁的小灯泡一闪一闪,像在节奏缓慢地呼吸。
屋里很安静。林思颖不在,卧室门半掩着,桌面干干净净,香薰换成了Jo Malone的节日限定,还在冒着一缕几乎看不见的白烟,是那种圣诞季限定的香型——红莓混着香草,甜得很刻意,却也很讨喜。
林念知蹲下来,把那颗歪掉的金星轻轻扶正了一点,没扶稳,又倒回来。她没再尝试,起身去厨房倒了杯水,坐在餐桌边,把手机掏出来翻了翻,刷到林思颖的IG Story。
今天的更新一如既往的精致。白天她和几个朋友在中环喝圣诞特调的咖啡,滤镜开得很柔,杯子上的奶泡用肉桂粉撒出个星星图案,文字写着:“tis the season.” 下面配了两个圣诞树emoji。
再往后滑,是她和朋友在铜锣湾某家dle shop合照,几根颜色不同的蜡烛立在玻璃桌面,标签印着法语,装饰的干花和绒布丝带一看就是“仪式感”的标配。最后一条是她穿着一件红色毛衣的自拍,滤镜调得像旧港片,笑容干净得近乎明艳。
林念知忽然有点想问她:“你是怎么做到的?”
怎么做到在一个星期前把自己摊开给人看,说自己想被爱、觉得自己是垃圾、甚至说过“我真的讨厌我自己”,然后一转眼又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,把生活打理得漂亮得体、光亮迷人,好像那个说“快死掉的小鸟”的人,是另一个人。
她关掉IG,把手机翻过来放在桌上,手指在玻璃杯边缘轻轻绕圈。她不是不理解林思颖的方式。相反,她太理解了。那种“不能让人看到自己软弱”的本能,藏情绪、藏伤口,把精致感与热闹感当作保护色,是很多人面对世界的方式。
但理解归理解,有些东西还是会像钝刀子一样硌着心口。
她不明白的是,为什么那晚发生的一切,只有自己一直记得?是不是只有自己,把那一夜的对话、那部《阿飞正传》,当成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而对林思颖来说,那只是一场情绪过载的临时出口?
她低头看了一眼手背,有点凉,玻璃杯在灯光下泛着白光。
餐桌那几个礼物盒大概是准备送给朋友的,包装得一丝不苟,林思颖的字贴在金色蝴蝶结下,“To Kary”“To Chloe”“To Agnes”,用的是那种英式花体,圆润漂亮,看得出是练过的。
没有她的名字。
当然,她也不意外。她们并不是“送礼物”的关系,虽然更近了,但可能还没到“节日互道祝福”的亲密程度。林念知一向清楚这类边界。她不期待,也不会主动。
可心里还是有一点点,说不出口的冷。
她知道这是自己的问题。她太容易把别人对她的“暂时性示弱”当成“永久性信任”,太容易在对方露出伤口后就想陪着包扎,可惜很多人只想“说完就走”,并不想被人陪。
也许她也是这样的人。只是自己说得少,所以忘了。
门铃在八点半响起,林念知抬头,有点意外。她走去开门,门一拉开,是林思颖,拎着两杯星巴克站在门口,头发有点乱。
“呃,我原本以为你会吃外卖。”她递过一杯,“但后来想想你可能连外卖都懒得点,又在随便吃速冻的,就顺便给你带了杯拿铁。”
“谢谢。”林念知接过,杯身还是热的。
林思颖走进屋,看到她盯着圣诞树,忽然笑了一下:“你不觉得它丑的挺可爱的吗?”
“挺歪的。”
“哎呀,那是因为你没调整它的‘情绪’。”她俯下身,把金星又拨正了一点,“它歪,是因为今年圣诞节大家心都歪了。”
“……你心歪了吗?”林念知随口问。
林思颖歪着头想了一下,笑着说:“早就歪了。”
她脱了外套,随手搭在沙发背上,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,丢到林念知面前。
“给你的。”她说得很随意,“今天在LOG-ON看到顺便买的。”
林念知一愣,看了眼盒子——是一只很小的白色便签本,封面是精致的织布质地,印着金色的英文字:“no one is ever really alone.”
“……这个是?”
“就是看到觉得像你啊。”林思颖拉开椅子坐下,咬着吸管喝自己的冷饮,“你不老是写写写吗?有时候你表情像别人欠你三十万。反正你喜欢写东西,就……写下来吧,别憋着。”
——
[镜头切换]
访谈地点:大围富健邨社区中心
受访者20:黄文乐,59岁,中学通识教师,香港本地人
——
那天的风很大。
林念知照常背着笔电,从大学站换乘东铁线,坐到大围。下午四点半,天已微暗,社区中心外面一排老榕树枝叶交错,掉下的黄叶在门前的地砖上堆了一角。她在自助饮水机旁接了一杯温水,推开一间静音会议室的门。
黄文乐早就到了。
穿着一件藏青色毛衣,脖子上绕着旧款的灰格围巾,黑边眼镜后面是一张有点疲惫但温和的脸。他站起来和她握手时,很有礼貌:“你就是林同学吧?辛苦晒。”(你就是林同学吧?辛苦你了。)
她笑了笑,打开录音笔,翻出访谈提纲。
“你说你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,小时候住哪里?”她问。
“观塘,裕民坊后面。”(观塘,裕民坊后面。)他回答得很快,仿佛这些年说过无数次,“以前啲楼冇冷气,夏天热到训唔着觉,一屋五个人,阿爸阿妈,我同两个妹。”
(以前的楼没有空调,夏天热到睡不着觉,一屋五个人,爸爸妈妈,我和两个妹妹。)
“你爸爸做什么的?”
“车房做学徒,后尾转行跑货车。好早出车,朝六晚十,返到屋企啲衫都系油味。”
(在修车厂做学徒,后来改行开货车。很早就出门,早上六点晚上十点才回家,身上的衣服全是机油味。)
“我妈以前喺街市卖菜,唔识字。”(我妈以前在菜市场卖菜,不识字。)
“佢从来唔识睇我啲功课,但会夹硬迫我温书,话‘读书唔叻就揸货车’,我听到呢句就怕。”
(她从来看不懂我的功课,但会强迫我读书,说‘读书不好就去开货车’,我听到这句话就害怕。)
林念知记下几个关键词:旧区成长、基层家庭、教育向上。
“所以你自己算是…靠教育向上流动的例子?”
“算啦。”他轻轻笑了一声,“我中学读得一般,入唔到U,去咗IVE,边读边做兼职,之后自己报副学士,再升上大学,读社会学。”
(算是吧。我中学成绩一般,考不上大学(U),去读了专业学院,一边读书一边做兼职,后来报了副学士,再升上大学,读了社会学。)
林念知一怔,抬头看他:“社会学?”
“系啊。”他点点头,“不过当时唔叫呢个名,好多人都笑我读呢科‘冇出路’。但我锺意,就读。”
(是啊。但那时还没叫这个名字,很多人笑我读这个科目‘没出路’。但我喜欢,就去读了。)
“嗰阵未兴鸡精补习班,我喺深水埗搵咗份教通识嘅兼职,学生冇几个,租晒唐楼三楼劏房做教室,楼梯冇灯,要用手机照上去。”
(那时候还没有流行高强度补习班,我在深水埗找了一份通识教育的兼职,学生不多,在唐楼三楼的劏房开课,楼梯没灯,要用手机照着上去。)
他说到这时笑了一下,像是苦中作乐:“我教书第一年,月薪一万三,交完房租之后净系剩两千几蚊。我拎饭盒返工,食一个星期一样嘅通粉,汤底加咗两次水都唔舍得换。”
(我教书第一年,月薪一万三,交完房租只剩下两千多块。我带饭盒上班,一个星期吃一样的通心粉,汤底加了两次水都舍不得换。)
“你有没有想过放弃?”
“有啊。”他说得很快,“试过好几次想唔做,但系一收学生评语就唔舍得。我记得有个S.4学生写:‘老师你好温柔,我系第一次听人解释社会点解会唔公平。’”
(有啊。试过好几次想不做了,但每次收到学生评语就舍不得。有个中四学生写:‘老师你很温柔,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解释社会为什么会不公平。’)
他说这句的时候,林念知看着他,感觉到一种淡淡但坚定的温度。
“我教咗十几年啦,依家系副主任。啲学生改朝换代,读书愈嚟愈大压力,我成日同佢哋讲——我哋嗰代人系靠捱出嚟,但你哋唔一定要走我条路。你哋要识得睇清世界,但唔好放弃相信自己。”
(我教了十几年了,现在是副主任。学生一代代换,读书压力越来越大,我常常跟他们说——我们那代人是靠吃苦撑过来的,但你们不一定要走我们这条路。你们要学会看清世界,但不要放弃相信自己。)
林念知点点头,问:“你觉得香港年轻人现在最难的是什么?”
他没有马上回答。窗外风声大了一点,风从门缝中挤进来,吹动会议桌上一张小传单的边角。
“系唔知自己系咪真系有出路。”他慢慢说,“啲人成日话香港冇希望,但我觉得希望唔一定系成就。有时希望系——你系咪仲愿意做好人,仲肯对身边人好。”
(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出路。人们常说香港没希望,但我觉得希望不一定是成就。有时候希望是——你是否还愿意做好人,还愿意善待身边人。)
“你讲呢个社会对年轻人唔公平,我认。但我唔希望佢哋变得咩都唔信。”
(你说这个社会对年轻人不公平,我认同。但我不希望他们变得什么都不信。)
他说着,把手中那支黑色中性笔转了一圈,接着说:
“你知唔知,我以前有个学生,家里住劏房,平时好静,有次交功课迟咗,仲跪喺办公室话唔敢讲原因。我问咩事,佢先讲原来嗰日冇电,成晚用手电筒温书。”
(你知道吗?我最近有个学生,家里住劏房,平时很安静。有一次交作业迟了,甚至跪在办公室说不敢讲原因。我问他什么事,他才说原来那天家里停电,整晚都用手电筒温书。)
“我听到个心都酸埋。香港去到今时今日,仲有人细路仔系咁样生活。”
(我听了心都酸了。香港到今天,还有小孩是这样生活的。)
“但系佢都冇放弃考试,成绩唔算好,但日日交齐功课,做晒笔记,字写得好靓。我话畀佢听,呢种人,将来唔会差。”
(但他没有放弃考试,成绩不算好,但每天交齐作业,做完所有笔记,字写得很漂亮。我跟他说,这样的人,将来不会差。)
他说到这里,声音轻下来。
“狮子山精神唔系要你变英雄。系叫你喺好艰难都唔屈服,唔害人,唔放弃自己。”
(狮子山精神不是要你变成英雄。而是要你在很艰难的时候不屈服,不害人,不放弃自己。)
……
她很想问,那如果是狮子山下的‘无脚鸟’呢?
但她没有问出口。
风一阵一阵地从窗缝钻进来,像从几十年前的旧楼吹到今天的社区中心。会议室的灯有点暗,桌上那张被风吹起角的小传单,是某个退休社工义务讲座的海报,印刷粗糙、纸边已经卷翘,角落写着一行小字:“重拾社区信任,从倾听开始。”
林念知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,又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下几句摘要。
黄文乐已经开始收拾东西。他动静不大,拿着那条灰格围巾在手中绕了一圈,又绕回原处,像是习惯性的反复确认。她忽然意识到,这个下午,她记录下来的,不只是数据与观点,更像是一段时间的残响。
“多谢你肯来听我呢啲旧人讲咁多。”黄文乐拿起保温杯,语气有点不好意思,“我啲讲法,可能唔够‘时尚’,你啲论文啲教授可能未必中意。” (谢谢你愿意来听我这种老人讲这么多。我的讲法可能不够时尚,你的教授未必喜欢。)
“唔会。”林念知站起来,微微笑了一下,“其实反而……我觉得你讲得好清楚。”
黄文乐点点头,背起包,临走前忽然停了一下:“你个题目系讲阶层焦虑?”
“系。”她答。
他想了想,说:“我哋嗰代人系‘冇得拣’,你哋系‘太多可以拣’,唔同。”(我们那代人是‘没得选’,你们是‘太多可以选’,不一样。)
“但唔代表你哋冇力量。”他看着她,轻轻一笑,“你哋而家写论文、做访谈、查资料,都唔系冇用。有人记录紧啲嘢,总有一日会有人睇见。”
“希望系咁啦。”她轻声应。
黄文乐转身离开,她听见他鞋底踏过地砖的声音,像从一段历史的尽头走出来。
……
她坐在会议室里静了一会儿。
风还在吹,落地窗外的黄叶一片片落下来,在夕阳残光中转出几道短暂的曲线。她没有急着走,只是重新打开笔电,点开那个就快完成的旧文档。
指尖停在光标闪动的位置上,她盯着那行标题:疫情后香港青年阶级流动的困境。标题是冷的,像城市建筑物外墙的金属板,但她脑子里浮现的是林思颖——沙发、靠垫、眼泪,还有那句“我只是想让人知道我还在”。
也浮现的是今天的黄老师,还有他说的那句“希望唔系成就”。
她突然意识到,她的论文写的是“阶层焦虑”,但她真正关心的,可能不是“能不能往上爬”,而是“人在中间时,是不是还能撑得住”。是不是还能不麻木、不躲起来、不失去爱人与被爱的能力。
不只是林思颖,不只是她自己,其实她访谈过的许多年轻人——有钱的、没钱的、本地的、港漂的——说到底,他们焦虑的,不是“没出路”,而是“找不到哪条路才是真正属于自己”。
光是“看清世界”已经太容易了,难的是“还相信自己”。
于是林思颖给的笔记本里有了第一行字:“活着已经够累了,但如果还能温柔,就已经是一种抵抗。”...